“老师,”我的学生问我,“现在真的还有林奕含那样的文学信仰吗?”
“有吧。”我多少有点不确定,但相信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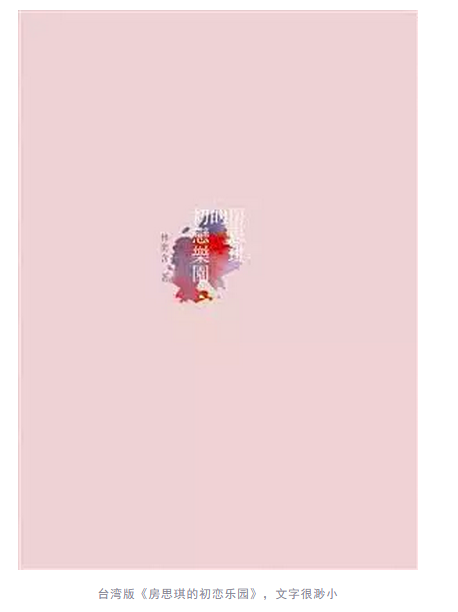
一年前的今天,2017年4月27日,台湾26岁的女作家林奕含在家中上吊自杀。在她生前出版的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林奕含讲述了“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房思琪等几位少女被补习班老师李国华诱奸、控制的故事。
如你所知,房思琪的故事里有林奕含自己的影子。
林奕含生前曾经就小说接受访谈,林奕含平静地述说创作经历与理念。除了那些被心理医生称为“经历集中营/核爆”的伤痛外,她提到了写这个故事让她感到“有一点屈辱”,而这一段话让人震惊:
“这整个故事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语境?为什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过五千年的传统?我想要问的是这个。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任何一个人的文字和为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正是这段话让学生问到了“文学信仰”。是的,在今日的大陆语境中,对“五千年的中文传统”是否还有人会如此热诚而焦灼地追问?会在意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对文学的背叛?
小说中的国文补习班老师李国华,正是借助自己对文学的熟稔与发挥,诱奸了13岁的女孩子房思琪。
对文学的信仰不止于此,为了摆脱被诱奸的耻辱感,房思琪不得不“爱上”李国华。林奕含自己说:“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

房思琪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都最崇拜老师。我们说长大了要找老师那样的丈夫。我们玩笑开大了会说真希望老师就是丈夫。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妳爱的人要对妳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所谓“爱”,所谓“思想”,其根柢就是对文学的信仰。从一开始,李国华能从周围讨厌凡俗的某先生某太太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跟许伊纹一样,在两个13岁小女孩的眼中,简直就是文学的象征:
“张太太继续讲,我就不懂小孩子读文学要干什么,啊李老师你也不像风花雪月的人,像我们婉如和她丈夫都是念商,我说念商才有用嘛。”
追求文学,本来就是进入反叛期的女孩们的一件武器。就像刘怡婷把吞吐海参说成自己其实并不太懂的“口交”,“无用”的文学,也是对大人们禁忌的一种冒犯。很不幸的是,当满身文学气息的李国华老师出现,房思琪的文学信仰变成了“逃离中的陷落”。
“怡婷很喜欢每周的作文日。单独跟李老师待在一起,听他讲文学人物的掌故,怡婷都有一种面对着满汉全席,无下箸处的感觉。”
怡婷与思琪轮流跟李国华单独学习,所以这也是房思琪起初的感受。这里我想插一句,26岁的林奕含还是不够老辣,她笔下的李国华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惊才绝艳,反而一开始就显得假惺惺又不懂装懂。但这是一种后设的视角,可是在13岁的房思琪眼中,李国华的形象应该高大得多,房思琪对李国华是一种压倒性的崇拜,这样后面的“爱”才能有一种“合理的反讽”。
本书的推荐人之一汤舒雯很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这本小说乍看谈论权力不对等之性与暴力,实际上更直指文学及语言如何成为诱奸与哄骗之物”。李国华就是这样说的:“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是学文学的人,我要知音才可以,我是寂寞,可是我和寂寞和平共处了这么久,是妳低头写字的样子敲破它的。”
房思琪信过这谎言,但她即使处于被诱奸被控制之中,她仍在成长,仍在质疑:
“有一次问他:‘最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呢?’老师回答:‘当初我不过是表达爱的方式太粗鲁。’一听答案,那个满足啊。没有人比他更会用词,也没有词可以比这个词更错了。文学的生命力就是在一个最惨无人道的语境里挖掘出幽默,也并不向人张扬,只是自己幽幽地、默默地快乐。文学就是对着五十岁的妻或十五岁的情人可以背同一首情诗。”
而李国华,一直在引导房思琪,在想像中把他们之间的不伦关系浪漫化,神圣化:
“他抓住她的手,得意突然羼入凄凉,他说:‘我跟妳在一起,好像喜怒哀乐都没有名字。’房思琪快乐地笑了,胡兰成的句子。她问他:‘胡兰成和张爱玲。老师还要跟谁比呢?鲁迅和许广平?沈从文和张兆和?阿伯拉和哀绿绮思?海德格和汉娜鄂兰?’他只是笑笑说:‘妳漏了蔡元培和周峻。’思琪的声音烫起来,我不认为,确切说是我不希望,我不希望老师追求的是这个。是这个吗?李国华没有回答。过了很久,思琪早已坐下地,以为李国华又睡着了。他才突然说,我在爱情,是怀才不遇。思琪心想,是吗?”
这简直是古今无行文人的惯用套路。房思琪骗自己这是师生间的爱情,有时她几乎快要相信了,因为相信对她有利,所以她“快乐地笑了”,然而这仍然敌不过最后的“是吗”。
我觉得《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令人惊异的地方,还不是女主角经历的惨不忍言,而是作者努力获得的那种冷嘲的笔调,而且是以第一人称!房思琪的挣扎就是作者的挣扎,但这种挣扎的结果,是窥破了诱奸犯的魔术:“在岛屿上留情,像在家里梦游,一点不危险。说书,说破她。文学多好!”
房思琪被逼疯了,但疯有时也意味着挣脱与清醒,正像汪曾祺说沈从文“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房思琪在日记那段用蓝色钢笔写下的“我要爱上老师”旁边,用红字标上了注解:“为什么是我不会?为什么不是我不要?为什么不是你不可以?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整起事件很可以化约成这第一幕: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
“他硬插进来,而我为此道歉”,是全书最狠的一笔,也是房思琪对世界最大的控诉:文学、修养、文明、传统,浩浩汤汤,没有人告诉她老师可以有多坏,人可以有多么虚伪,而“为文化所化之人”在这虚伪与恶面前,会多么的孱弱与屈辱。

想清楚这一点之后,房思琪疯了,而林奕含还在世间挣扎,她在文字里质疑与嘲讽文学,但又将书写当成了最后的救赎。她对自己的精神医生说:
“文学是最徒劳的,且是滑稽的徒劳。写这么多,我不能拯救任何人,甚至不能拯救自己。这么多年,我写这么多,我还不如拿把刀冲进去杀了他。真的。”
林奕含对文学的信仰,或许是她陷落的起因,但也是她最后的堡垒。房思琪不再相信李国华的巧言令色,可是林奕含还在冒险,她还在挑战文学的限度,看文学能不能帮她摆脱屈辱与痛苦,像很多人讲的“说出来,就没那么受伤”,可是她写出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仍然没有办法求得解脱,反倒像印证了张太太的话:
“张太太把手围在李老师耳边,悄声说:我就说不要给小孩子读文学嘛,你看读到发疯了这真是,连我,连我都宁愿看连续剧也不要看原著小说,要像你这样强壮才能读文啊,你说是不是啊?”
“读文”需要“强壮”,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但放在这本小说的语境里,相信文学的人虚弱,而以文学为诱奸工具的人强壮。“她们的第一印象大错特错:衰老、脆弱的原来是伊纹姊姊,而始终坚强、勇敢的其实是老师。从辞典、书本上认识一个词,竟往往会认识成反面。”
“她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辜负了她们。”

我没有想在周年的时候强猜林奕含的死因。那应该是异常复杂的原由。但是,如果我们要讨论的不是一出狼师性侵的社会新闻,而是一位受害者戴上小说的假面,跳了一支天鹅之死的绝唱。那么,文学信仰的成立与坍塌,将是这场阅读与讨论的关键词。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