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蕾、秋水:
都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月读《儒林外史》的主题是“朋友”,正好7月1日就去上海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主题是“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参会论文时间跨度从唐代到1980年代,每个时代的交游,都是各有各的精彩,有的是友谊,有的是交际,有的是应酬,有的是共同体……所以“朋友”两个字,里面的内涵非常复杂。
《儒林外史》提到“朋友”二字有多少处你们知道吗?我数了一下,共有105处!这是高频词无疑了。那书里的“朋友”都有哪些含义呢?我先来理理。

◉五代《文苑图》卷的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第一回说王冕“也不交纳朋友”,那么像秦老这样的民间友善人士,就不算朋友了?通观《儒林外史》,还真有这样的设定,第五十五回写一个叫荆元的裁缝:
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余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也极喜欢作诗。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和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也就不和他亲热。
但同一回又说曲中知音于老者是他的“老朋友”,可见未可一概而论。但总的来说,“朋友”两个字在吴敬梓笔下有着复杂的含义,它在回目中出现过三次,分别是第九回“娄公子捐金赎朋友”,第十八回“访朋友书店会潘二”,第三十三回“迟衡山朋友议礼”。前两回是什么样的朋友,读过《儒林外史》的朋友都能明白,而最后一次,迟衡山“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这里的朋友显然是价值观层面的知己,迟衡山前面所言“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作礼乐”,讲举业的朋友也是“朋友”,志趣相投的也是“朋友”,这其实就是“朋友”这个语词的两面性。我在谈《红楼梦》时引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末尾的两句诗,道是“春风满面皆朋友,欲觅知音难上难”,也是这种对比,“朋友”与“知音”对举,可见前者外延远广于后者。
“朋友”本来就是合称。《礼记》有云“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同门,只是同一个老师——如果是自己选的老师还好说,像科举中的“座师”“房师”,那简直只是仪式性的关系(但又很结棍,大有用场),所以“同年”,在传统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但又扯不上“同志”,只是属于同一时空同一群体。《诗经》里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就只能用“友”不能用“朋”,那么《论语》里的“有朋自远方来”“无友不如己者”是否也是如此严格的定义?这样咬嚼下去,倒也有趣,比后世大而化之地谈论朋友——所谓八大借口,其中一条就是“都是朋友”,指称要有效得多。语词总是在不断地泛化淡化,像“哥”“姐”也曾是非常严格的称呼,后来用作尊称,也是非常郑重的事,如今则随便接个推销电话,也是“哥”“姐”盈口,今天还接了个,开口就是:“哥,最近不忙吧?”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这种风气,有点像食材越难新鲜,制作越要麻辣重口,社会关系越是疏离,嘴里喊的就越是亲热,客服喊“亲”,同事间呼“宝贝”已是常态,也是称呼古今异变之一斑。
扯远了,说回《儒林外史》,“朋友”其实也是当时的一种特定称呼,如“梅朋友”“魏朋友”,第二回有说明:“原来明朝士大夫称儒学生员叫做‘朋友’,称童生是‘小友’。比如童生进了学,不怕十几岁,也称为‘老友’;若是不进学,就到八十岁也还称‘小友’。”梅玖还补充说“我们学校规矩,老友是从来不同小友序齿的”,科举层阶替代了长幼伦理,成为一种新的等级秩序,这是“老友”“小友”这两个不同的称呼传递出的意味。
倒是两位不得中举的娄氏公子,对“朋友”的理解颇有古风:“朋友闻声相思,命驾相访,也是常事。”(第九回)虽然他们结交的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都很难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二位娄公子用钱赎了杨执中,却不愿在他面前提起此事,确实可算不堕俗情。娄公子们虽然迂执可笑,这一点倒是读书的好处,他俩属于可交之人。卧闲草堂此回评语道:“娄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迎之致敬以有礼,岂非翩翩浊世之贤公子哉?然轻信而滥交,并不夷考其人平生之贤否,猝尔闻名,遂与订交,此叶公之好龙,而不知其皆鲮鲤也。”——这就近似那个常见的问题:富人附庸风雅,要不要得?我是支持一切附庸风雅的,因为附庸风雅,至少认可风雅的高价值,附庸着附庸着,交了许多学费,吃了许多苦头,未尝不能变为真风雅。怕的是以俗为雅,或求俗弃雅,一个社会,风雅总是小众行为,也代表一些有别于主流众趋的可能性。追求这种可能性,总比全然反对这些可能性要好一些,你们说是不是?

◉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照
《儒林外史》中最为人称道的朋友,莫过于马纯上马二先生为朋友出头,还有鲍文卿与向鼎跨越阶层的友情。前者是单向的,只见他对朋友好,对没有回报的友谊,也坦然处之,因此更是难得。马二先生要敲诈蘧公孙的衙役说道:“你同他是个淡交,我同他是深交,眼睁睁看他有事,不能替他掩下来,这就不成个朋友了。但是要做的来。”“但是要做的来”这六字精妙,如果没有这六个字,马二先生就成了仗义疏财不顾后果的杜二先生了。衙役嫌马二先生的出价低了,马二追加的说辞也很有意思:
况且你们一块土的人,彼此是知道的,蘧公孙是甚么慷慨脚色,这宗银子知道他认不认?几时还我?只是由着他弄出事来,后日懊悔迟了。总之,这件事,我也是个傍人,你也是个傍人。我如今认些晦气,你也要极力帮些。一个出力,一个出钱,也算积下一个莫大的阴功。若是我两人先参差着,就不是共事的道理了。
不能不说马二先生也是世情练达又心存厚道的好朋友。他明知道蘧公孙不是什么慷慨角色,仍愿一力替他承担化解这可能谋逆的罪名——知道清庄廷鑨明史案的话,就知道马二先生摊上这事,风险不小。便是那差人有心勒掯,也不得不说一声“先生!像你这样血心为朋友,难道我们当差的心不是肉做的?”原文还有许多讨价还价的精彩,不多抄了,总之,这件事算是马二一力担当化解,而他把箱子还给蘧公孙时,也不过说了声:“而今幸得平安无事,就是我这一项银子,也是为朋友上,一时激于意气,难道就要你还?”蘧公孙呢,果然不是什么慷慨角色,虽然当下又是纳头拜了四拜,又是告知乃眷备饭,还说:“像这样的,才是斯文骨肉朋友!有意气!有肝胆!相与了这样正人君子,也不枉了!像我娄家表叔,结交了多少人?一个个出乖露丑,若听见这样话,岂不羞死?”(我读书时就一直想:那你倒是还钱哪!人家批时文三更灯火好辛苦的!)结果次日听说马二要走,蘧公孙又是留他来家住,又是办酒席饯别,都是虚话,真正到送别之时,也不过是“封了二两银子,备了些薰肉小菜”,还“要了两部新选的墨卷回去”,全不见当日拿收账来的二百两银子周济犯官王惠的家传慷慨,也不知道是不是结婚生子当了编修赘婿的缘故。

马二先生除了仗义之外,还有一般好处是心大。你看洪憨仙洪老师诱他入局,借他来骗胡三公子,不料洪憨仙自己突然病死了。马二先生回想起来,反而是“他亏负了我甚么,我到底该感激他”,拿出洪憨仙给的银子来,“备个牲醴纸钱,送到厝所,看着用砖砌好了”,剩的银子,还打发了四位伴随上路。可能有人觉得马二先生有些滥好人了,但这般厚道的一个人,不是哪里都能遇到的。
与马二先生完全相反的,当然是匡超人。这个人在自家父亲面前是孝顺的,在事业上是上进的,但只是对待朋友的那一副嘴脸,实在让人恨得牙痒痒。匡超人与潘三的关系,要从潘保正说起。匡家失了火,是潘保正帮匡超人去庵里央和尚租的房,说法是:“师父!你不知道,匡太公是我们村上有名的忠厚人;况且这小二相公,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你出家人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权借一间屋与他,住两天,他自然就搬了去。香钱我送与你。”帮匡家出香钱不算,匡超人拜知县为师,是潘保正拿的手本,匡超人有了知县老师,眼角高,不肯拜学里的教官,也是潘保正劝导,李知县坏了事,还是潘保正来劝匡超人出外暂避,听说他想去杭州,专门介绍自己的“房分兄弟”潘三——这一介绍,就弄出一番事来。
潘三不是什么好人,他请匡超人上街吃饭,穷形尽相地绘出了一个胥吏的横行霸道:
当下吃了两个点心,便丢下说道:“这点心吃他做甚么!我和你到街上去吃饭。”叫匡超人锁了门,同到街上司门口一个饭店里,潘三叫切一只整鸭,脍一卖海参杂脍;又是一大盘白肉,都拿上来。饭店里见是潘三爷,屁滚尿流。鸭和肉都捡上好的极肥的切来,海参杂脍加味用作料。两人先斟两壶酒,酒罢,用饭。剩下的就给了店里人,出来也不算账,只吩咐得一声:“是我的!”那店主人忙拱手道:“三爷请便!小店知道!”
潘三看到潘保正份上,对匡超人确实不坏,让他抽头钱,教他假造公文,冒名替考,带挈匡相公发了财,又介绍衙门郑老爹的女儿与他为妻。在潘三的世界里,这也是一等一的善待朋友了。这十九回的回目叫《匡超人幸得良朋》,不完全是反讽。但在潘三横遭祸事之后,匡超人是如何对他的呢?蒋刑房替潘三传话,想“会一会,叙叙苦情”,匡超人的第一反应是去看潘三是“赏罚不明”,蒋刑房听得出奇,揶揄他说:“这本城的官,并不是你先生做着,你只算去看看朋友,有甚么赏罚不明?”匡超人居然面不改色,说出了一篇大道理:“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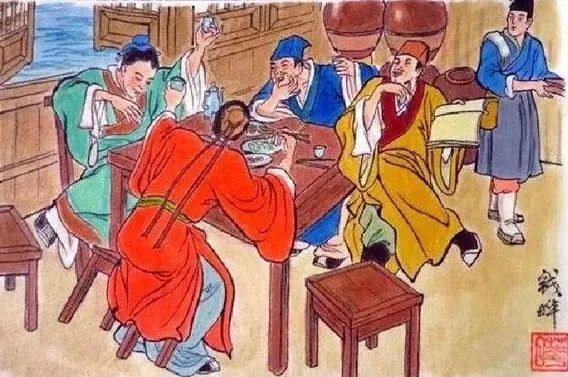
这一段我从小到大,已经看了有百八十遍,而今重读,仍然觉得不寒而栗。一个人,还是个读书人,怎么能无耻到这般田地?想来这种情感是古今共通的,卧闲草堂的回末评极为辛辣讽刺:
潘三之该杀、该割,朝廷得而杀割之,士师得而杀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杀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杀割之,斯时为超人者,必将为之送茶饭焉,求救援焉,纳赎锾焉,以报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为代朝廷行赏罚,且甚而曰:“使我当此,亦须访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虫螫毒未有过于此人者。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天下之人如尽是匡超人,那还谈什么朋友?这是三百年前吴敬梓的一声浩叹,一直幽幽地传到了今天。
能够提振我们对友谊信心的,莫过于鲍文卿与向鼎的“忘阶之交”了。故事的开端是戏子鲍文卿在按察司替向知县讨饶,按说这是犯忌的事,但鲍文卿的理由是:“自从七八岁学戏,在师父手里就念的是他做的曲子。这老爷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如今二十多年了,才做得一个知县,好不可怜!”这让按察司也动容不已,遂了他的愿,还写信给向鼎,为鲍文卿要几百两银子的谢礼。
但鲍文卿打死不肯收向鼎的谢礼,而且话说得非常决绝:“这是朝廷颁与老爷们的俸银,小的乃是贱人,怎敢用朝廷的银子?小的若领了这项银子去养家口,一定折死小的。大老爷天恩!留小的一条狗命!”我们现在看这番话,会觉得鲍文卿骨子里是个奴才,但在《儒林外史》的时代,这是一种美德,叫作“安分”。即卧评所谓“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乃晚近之士大夫,往往于歌酒场中,辄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也,脱俗也,而此辈久而习惯,竟以为分内事”,这种阶级意识,是那个社会的积习,我们看着虽不舒服,但亦无足怪。

难得的是,吴敬梓写了一个义伶,又对照着写了一个义官。向鼎是一个肯写戏的官,他有可以跨越阶层的意识。他在街上偶遇鲍文卿,立即让人请他来会:
向知府已是纱帽便服,迎了出来,笑着说道:“我的老友到了!”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向知府双手扶住,说道:“老友!你若只管这样拘礼,我们就难相与了!”
当然,向知府也有不能免俗的地方,如夸赞鲍文卿的义子鲍廷玺,说的是“好个气质!像正经人家的儿女”,言外之意优伶并非正经人家。但他对鲍文卿的敬重是真心的,鲍文卿不受贿赂而说情,巡考场又能与人为善,向鼎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向同官介绍鲍文卿时如是说:
后来渐渐说到他是一个老梨园脚色,季守备脸上不觉就有些怪物相。向知府道:“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
君子与否,与职业良贱无关,这是吴敬梓要表达的人物观。子曰“礼失求诸野”,也未尝不能是这个意思,“仗义每多屠狗辈”,虽是愤激语,但其实社会上稀缺的不是仗义的屠狗之辈,而是因为仗义就能平视、高看屠狗之辈的达官显贵。

所谓“一生一死,乃见交情”,鲍文卿去世后,向鼎来吊孝那一段,也是年轻人说的“太好哭了”。这里也特别能见出《儒林外史》的好处,内在感情无论如何浓烈,写来总是淡淡的白描:
向道台道:“我陛见回来,从这里过,正要会会你父亲,不想已做故人。你引我到柩前去!”鲍廷玺哭着跪辞。向道台不肯,一直走到柩前,叫着:“老友!文卿!”恸哭了一场,上了一炷香,作了四个揖。鲍廷玺的母亲也出来拜谢了。向道台出到厅上,问道:“你父亲几时出殡?”鲍廷玺道:“择在出月初八日。”向道台道:“谁人题的铭旌?”鲍廷玺道:“小的和人商议,说铭旌上不好写。”向道台道:“有甚么不好写?取纸笔过来!”当下鲍廷玺送上纸笔,向道台取笔在手,写道:
皇明义民鲍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顿首拜题。
向鼎由知县到知府到道台,对鲍文卿从感激到敬佩到相知,二人的友情跨越阶层,却善始善终,卧评道是:“向观察哭友,堂皇郑重,可歌可泣,乃颜鲁公作书,笔力直欲透过纸背。”这一段描写,这一份交谊,代表了人类对于超功利友情的永恒向往,经见的世事越多,认识的朋友越众,反而会更稀罕这样的真心以待。

在这封信一开头提到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会议上,我和学生王朴微联名提交的论文题为《“烫人”的友谊——〈文汇月刊〉呈现的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交游》,这是在王朴微硕士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有感于1980年代“友谊”的特殊性,而爬梳撰写的文章。论文的结尾写道:
八十年代那“烫人”的友谊,在如今为何引人怀念,其中原因是复杂的。在许多人看来,当下中国人际关系中充斥的是充满冷漠、自私、误解与唯利是图的风气,换言之,当下的中国人越来越难以安置精神与主体、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八十年代的纯真友谊成为人们悲叹现实的对照,它的逝去仿佛正如一个悲剧不得不以死亡结尾一般自然。但我们却应追问,究竟是什么,让后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心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巨变?究竟是什么,让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看似坚不可摧的友谊最终变质?
一句“人心不古”并不能解释为何80年代纯洁与烫人的友谊无法在今日复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1980年代知识分子交游的特殊性,源自于彼时的文化氛围,源自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身份认同。当我们今天在怀念80年代的友谊时,或许更应思考的是,是什么土壤培养出了这样烫人的友谊?这些土壤为何最终消失?如今有无可能(甚至有无必要)让这些土壤“死灰复燃”?
不同时代的情感或许可以共通,三百年前吴敬梓用小说惋叹纯真友情的消逝,三百年后我们用论文唏嘘“烫人”友谊的不再,其中都寄寓着对“正常的”人际关系的认定与眷恋。不知道这些感慨有没有让你们想起那些曾经温暖的名字,曾经无所顾忌的笑声?
盼回信。
杨早
2023年7月13日星期四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