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995,1998,2003,2009,2013)及第四届思勉原创奖(2017)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代中国人文观察》《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等三十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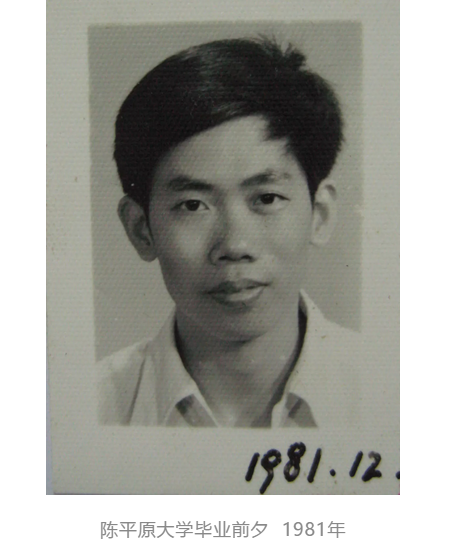
201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60岁生日时,他的夫人夏晓虹教授收集了20余年来他的众弟子发表的、有关他的著作的书评,汇成《弟子书》以为贺礼。书册中附有一张书签,上面抄了陈平原2009年《另一种学术史》里的一段话:
“假如承认好学者大都‘学问’背后有‘情怀’,而不仅仅是‘著述等身’,那么,最能理解其趣味与思路的,往往是及门弟子。理由很简单,亲承音旨,确实给了弟子更多就近观察的机会,使得其更能体贴师长那些学问背后的人生。”
作为其及门弟子之一,笔者来写陈平原教授,“就近观察”大抵是有的,“客观公正”则基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成心谄谀或是为尊者讳,而是弟子的立场、学风的传承、关系的亲疏,都会影响将老师与同时代人相比较时的眼光。只能自勉“有一说一”,写写笔者心目中的陈平原教授的形象。

2018年11月30日,第十二届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揭晓,陈平原的新著《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入选其中。而且,这本书还被评为“年度推荐书”。评委会给出的推荐语是:“作者积二十年之功,搜集史料,解说‘画报’,本书是集中成果的展示。借画报的图像叙事的研究,纳社会风俗、文化思潮、审美趣味于一书,对西学东渐、中外互动、古今对话有了具体而微的发现,从而走进晚清历史的幽微之处。本书聚焦一点,触角却很多,在这方面的研究,作者虽不居开创地位,然而,它的很多篇章却有示范之力,也必将影响今后的同类研究。”
有意思的是,这本厚达500多页的巨著在参与评选时,并非被归入“人文”或“文学”,它所属的分类是“艺术”。这个小细节传递出的内涵很丰富,正如陈平原此前的“大学五书”等多种著作直指中国高等教育一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似乎又是一次“跨界”的冲击。对于以“文学史家”名世的陈平原来说,他的学术研究,还有多少种可能?

与友人首倡“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虽然早在1978年4月,陈平原就已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但作为“金七七”(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正式得到学界的注目,是1985年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读书》发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此时,陈平原尚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王瑶,攻读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二字,现在多被人理解为时间概念,即1919至1949年,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重合。然而,当陈平原的导师王瑶创设这一学科时,“现代”强调的是这一范畴的革命性与创新性。王瑶的奠基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书名中的“新”字就能说明这一用意。
而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共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则在当时最大可能地摆脱了“革命性”“人民性”等文学史的窠臼,将从晚清到“新时期”的中国文学打通理解,展现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个侧面:欧化与民族化,创设了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以“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创造,都必须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
现在很难想象这样一些听上去平平无奇的观点在当时引发的巨大冲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当中,多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代表了学界对这种观念的认同。近年,在各大学的文学院或中文系中,很多都实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合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需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与研究,也已成为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
然而,这并不是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真的能达到陈、钱、黄三者的原初设想。将观点与标准贯彻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去,要面对的问题尚有许多。最明显的如严家炎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的写作,担纲各卷的作者如陈平原、严家炎、吴福辉、钱理群、洪子诚,都是一时之选,五大卷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也早早编就,但三十多年过去,也只有陈平原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得以面世。据说其难点在于,陈平原描述晚清小说发展的第一卷,研究方法如“消解大家”“打通雅俗”“注重进程”“叙事模式”等等,似乎很难应用于“现代文学”(新文学)的研究。这其中的纠结,反映出的或是陈平原与学界主流之间的差异性。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
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准备考现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时,跟读本科时的一些老师讨论过选择导师的问题。一位治政治学的教授极力建议笔者报考陈平原教授的研究生,他的理由是:陈平原的研究成果能够为更多的人文社会学科共享。
在20世纪80年代,陈平原之声名鹊起主要是因为他的小说史研究(尤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深受同行好评)。延至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以《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小说史:理论与实践》,进一步深化与拓宽自己的小说史研究,而在他的事业中,更让知识界瞩目的,应该是《学人》辑刊的创办,那也引领了后来被人概括为“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精神生活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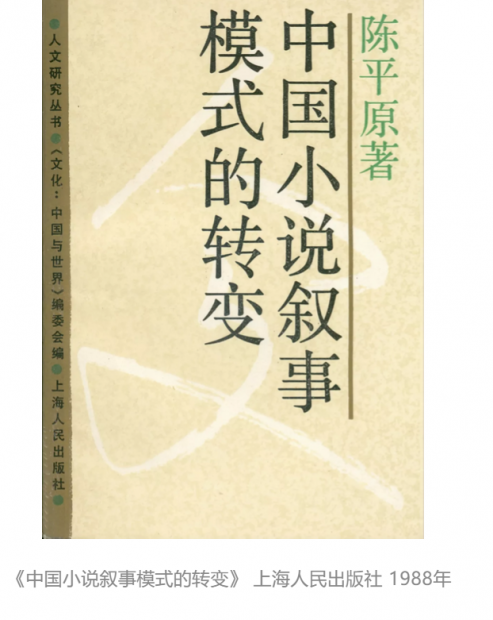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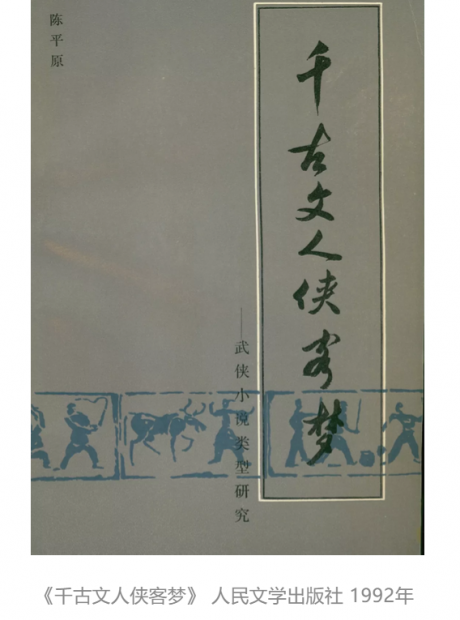
1991年诞生的《学人》集刊,至2000年共刊行15辑,主编由陈平原、汪晖与王守常轮流担任。这份由日本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提供资金支持的集刊,可称是对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时知识界风气转型的集中体现。与20世纪80年代张扬、宏大、以高谈阔论为时尚的风气不同,《学人》集刊象征着学界风气转为收敛、内省、以恪守规范为标尺。学界的共同偶像或曰“文化英雄”似乎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梁启超、鲁迅、胡适等“思想家”,变成了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问家”。
陈平原在《学人》等刊物上发表的论文,1998年结集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出版。这些论文铸就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的学术形象。有评论称这些篇章:“对于近年中国学界之注重学术史研究,起了引导的作用。”陈平原则自称:“在我的学术论著中,这本书写得最艰难,从1991年写到1997年,行程竟六年有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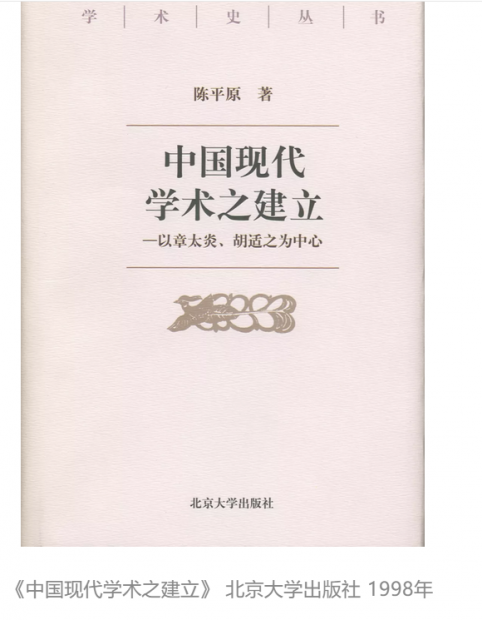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比较全面地展现了陈平原的学术史思路,即强调“西学东渐”与“旧学新知”的双重视角。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注重的“世界化—民族化”思路如出一辙。因此它也代表了陈平原对于近代中国的基本认知:既承认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但又时时留意文化传统内部的变革动力,以及最终“中国现代学术”得以成形的曲折与复杂。
比较十年前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现代学术”两种思路的异同,可以说,陈平原在导师王瑶去世后,接手“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学术工程,在其中起到了过渡与缝合的双重作用。正是在集合同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陈平原对基于“新/旧文学”二元对立的“传统与现代”叙事框架,做了很大的调整。他不再说“西学剪裁中国文化”,更强调“对话”而非“对峙”。换言之,以前认为的“旧”,未必就是真的“旧”,从前看好的“新”,也未必是那么纯粹的“新”。较之20世纪80年代简洁明快的结论、痛快淋漓的对传统的批判,这样小心翼翼地试图重释“传统”,明显不那么合乎追求简明的公众胃口。或许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术日益专业化、圈子化的重要原因。

大学不是“办”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
笔者考入北京大学读研,是在1998年9月,而那一年的5月4日,是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盛大校庆前后,也有阵阵舆论热潮。
因为这一年他主编的《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与独撰的《老北大的故事》,陈平原被众多媒体称为“校史专家”。他又进而出版《北大精神及其他》《中国大学十讲》,到2016年时,则出齐《大学有精神》《大学何为》《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大学新语》等“大学五书”(含《老北大的故事(修订版)》),此外尚有《“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花开叶落中文系》《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等随笔集。可以说,21世纪公众印象中的陈平原,大多数时候都以“大学教育专家”的面目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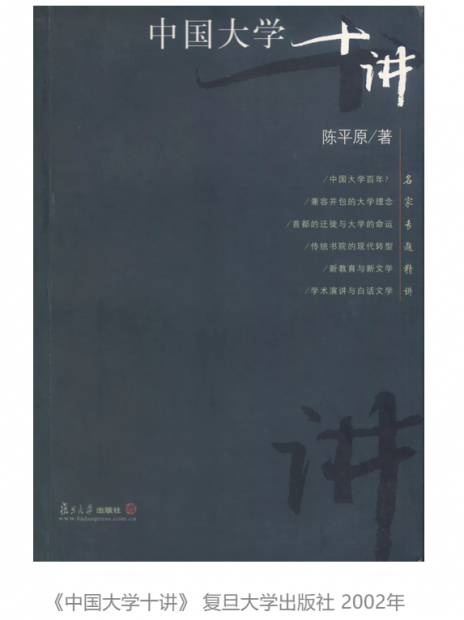
陈平原进入大学史的契机,最初应该是1994年访学东京大学。适逢东京大学百年校庆,相距不远的北大百年校庆正可以与之成为一种对比。与日本大学的资料保存与研究相对完备不同,在中国,即使是北京大学,校史上也有诸多模糊不清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包括校庆日期、英文译名、人事关系等等。之前中国研究教育史的学者重视的往往是制度史,如高等教育政策、机构沿革与变迁,还未有像陈平原那样将一个大学的历史置于教育史、文学史、学术史与政治史的多重脉络中来考察的。
事实上,学者坚持的是对事实的还原与理解,而现实未必能包容这种对事实的探求,关于“北京大学校庆日期”的考订就惹出了不小的麻烦。虽然陈平原只是在考辨史实后指出:北京大学的创建日期,既非民国时期使用的12月17日(那是京师大学堂重开的日期),也非当下沿用的5月4日(那是1953年才改定的,之前只是校友返校日),而是1898年12月30日。然而《北大校庆,为何改期?》探索校庆改期原委,并指出:“北大之修改校庆纪念日,固然有利于弘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却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其危险即在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考据”。陈平原反问:“倘若有一天,‘五四’不吃香了,怎么办?难道说,另外选择一个光荣的时刻?”他的这一系列文章后来也引发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仅从这个细节,足以看出陈平原治教育史与别家不同。一方面,他关注现代以来的“大学精神”。制度只是表面,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在创校伊始便风格不一,制度的调整只因应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也与各自不同的定位与社会影响有关,这也是通常人们说的“校格”。
讨论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陈平原也不主张仅仅拿出西南联大这样的高校神话,而是针对诸多内迁大学汇成的“教育奇迹”,总结出足以启示当下高等教育的三点:“第一,以教学为主;第二,注重师生关系;第三,坚持学术标准。”
另一方面,陈平原主张治教育史亦须恪守学术规范,不能急于“古为今用”。而今整个社会对于中国大学的期望与想象,都远远超过了大学所能承载的。诸多文章不惜美化、神化民国大学,借以针砭当下高校的“弊病”。陈平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现在有一种流行观点,说民国大学多好多好。可以持论者必须明白,今天的中国同样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民国大学是一种精英教育,这与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模式很不一样……当下中国大学的困境必须直面,不是召唤‘民国大学’的亡灵就能解决的。”(《大学新语》)
规模讲述国内大学的“故事”,由陈平原、夏晓虹合编的《北大旧事》可为代表。自此之后,大学、大师轶事纷纷传扬。这或许实现了陈平原期许的“借助老大学故事的讲述,体贴并领悟真正的大学精神”,但作为资深的文学研究者,陈平原亦深知“故事”里虽然蕴藏着历史与文学之张力,但同样也埋藏着容易让人失足的陷阱。
陈平原提出的“大框架不能动,小故事则多多益善”的标准,意味着对“大学精神”需要一种整体的把握,即:大学不是“办”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一个国家的大学,必须兼具“本土视野”与“国际情怀”,否则不是固步自封,就是邯郸学步,百余年来这样的教训数不胜数。而小故事无论真伪,体现的往往是该校师生乃至整个社会对教育理想的向往与塑形。“讲故事”当然是好的,但不能根据需要编故事,也不能只讲选择过的故事。惟其“多多益善”,才能在纷繁复杂中觅得真谛。

一手操持学术研究, 一手挥洒散文随笔
2001年,陈平原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一则短文《有情怀的专业研究》。此文虽短,陈平原却对自己的学术理想做了定性——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扬万里而学风空疏,20世纪90年代的“更强调学术规范”,就是要为问题的讨论设置专业的门槛,使讨论不致沦为低水平的感悟汇编。而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专业主义”渐渐成为塑造学界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但那同样又会给各种奇思妙想,甚或现实关怀带来极大的压抑。陈平原的理想,则是“用‘情怀’来补‘规则’的缺失”。
这种理想,说大一点,针对的是“边缘”与“中心”的复杂关系:专业化有助于提升“边缘”的对话能力,使其能渐次进入“中心”,并表现出应有的冲击力;但对“中心”的警惕,可以保持“边缘”的活力,不致让“边缘”为“中心”轻易收编,成为新的“中心”。
笔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后,一次在电梯口遇到一位已退休的《文学评论》老编辑。旁人向其介绍我,说是新来的研究人员。老编辑问是谁的学生,知道答案后感慨了一句:“陈平原的学生,那是不会忽悠学问的喽。”笔者对此事印象极深。
所谓“专业主义”,用处无非是提升自身的学术信誉,从而降低学术场中的交易成本,让同行不必再费心清理论文中非学术的成分,避免种种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带来的干扰。从这个意义上说,“专业主义”仍是当前学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反过来说,近年提倡的“专业化”,同样也衍生出大批闭门造车的论文、自说自话的会议,以及孤芳自赏的圈子。就整个公共空间而言,“专业壁垒”一是隔绝了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造成如前述“为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共享”的例子日见减少;二是隔绝了专家学者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专业学者只在课题、会议与论文专著之间打转,而公共空间的发言则让渡给裹挟公众情绪的“意见领袖”,这正是近十年舆论场的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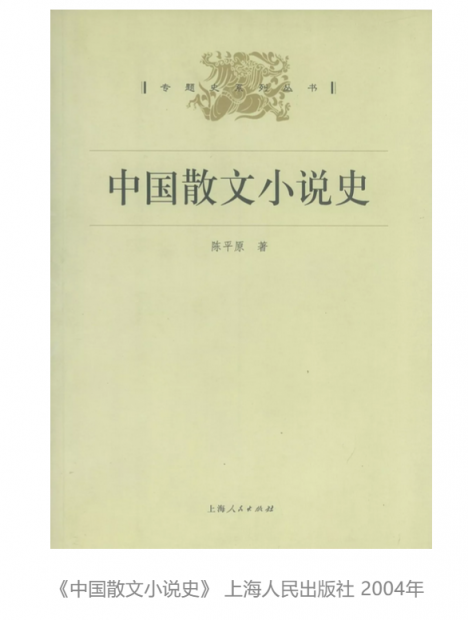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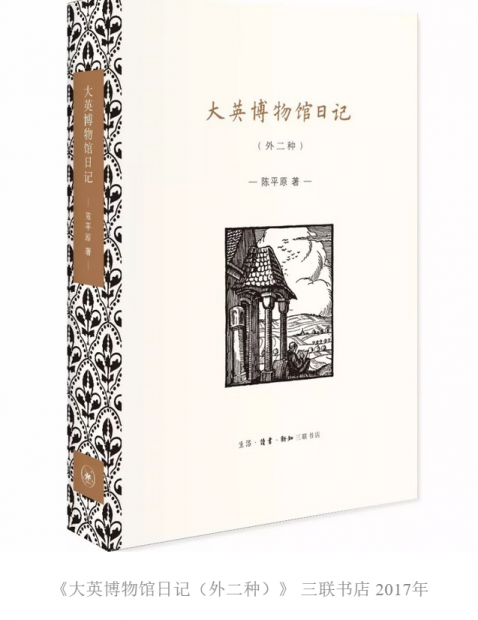
陈平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走向封闭”的危险。他早年提倡“两副笔墨”,即一手操持学术研究,一手挥洒散文随笔。除了大部头专著之外,他的《阅读日本》《学者的人间情怀》《掬水集》《漫卷诗书》等随笔集亦颇受欢迎。
1998年后,陈平原又开始倡导并践行“第三种笔墨”,“不是专业著述,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文随笔,而是半学术半文章。”“希望沟通文与史、雅与俗、专家与大众、论著与随笔,将历史研究的探索与写作方式的革新结合起来,希望兼及‘文’与‘学’”。
在笔者看来,追求文章的兼及雅俗,还是陈平原作为一名“文人”或“公民”的自我担当。陈平原真正为人所不及之处,还在于其从文学史专业出发,进而对大学、图像、声音等诸种领域的近乎全新的探索与深掘。或者可以总括一句:他对构成近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极感兴趣,并努力将这种“兴趣”转化为“学问”。
以陈平原撰写《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他选编《〈点石斋画报〉选》,与夏晓虹合撰《图像晚清》,为报纸撰写专栏“看图说书”,在晚清画报领域确实有超过二十年的持续关注与深入研究。这种一开始可能是碎片化的、个案式的研究,一步步走来,汇成《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一书。书中牵涉从晚清到民初的画报120余种,重点论述其中的30多种。涉例既广,又并非胪列种类、记录资料,更不是囿于“讲故事”,而是希望“发凡起例”,建立一种研究画报甚至是图像的模式,自己或旁人都可以因之为据,继续扩展这一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这本著作对于曾经边缘的“图像研究”,是一种整体的提升,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对陈平原个人研究领域的拓展。近日,该书又入选“文津图书奖”。
笔者离开北大已有十多年,也有了自己认定的治学领域,唯能时时牢记、常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其唯“有情怀”与“专业”的互补与互动乎?
2018年,由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三位在20世纪80与90年代之交编选的“漫说文化”丛书再版,笔者组织了数场读书会。在与嘉宾、读者的交流中,更能体味几位老师当年的努力。他们在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种宏大构想之余,仍要费心劳力,编选十册“漫说文化”,希望借助现当代名家散文,重现近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拼图。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焦虑,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但有些努力的方向与坚持的意义,仍然永恒。
原文刊载于《文化月刊》杂志2019年5月号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