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又是周末了,又到了我们盘点的时候,小说民国也进入了倒计时,这是倒数第六篇小说了。咱们一年的阅读就快到头了,回顾一下,我觉得挺好的。最早我们提出创意的预想——希望大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从自己自身出发,去关注民国小说——我觉得基本上是做到了,尤其是最近萧红的阅读当中,你可以明显看到,哪怕是《马伯乐》这么一个比较偏门,“萧红作品选”很多时候都不会选的作品,但是大家仍然从中读出了很多人生的况味和内心的纠结,认知到这是一部多面的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难得的。
萧红的才气当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觉得各位参与者阅读上面的长进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旁观的没有参与的人,可能会没有那么强烈的体会。所以我建议以后有这种机会,大家还是参与一下,这样跟着读下来,我觉得是痛并愉快的一件事情,包括他们在群里讨论关于萧红的真诚,关于性别的差异,关于作家是否将事实逻辑化的问题,没有在公号里反应出来,但是颇有趣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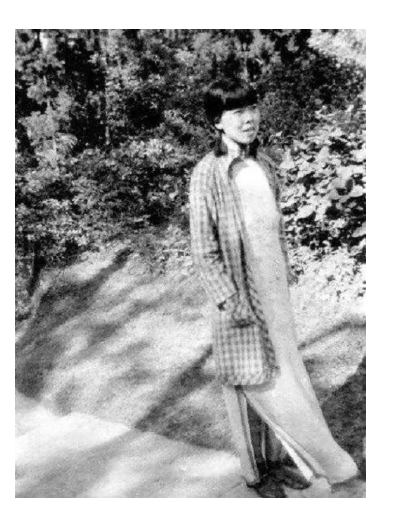
下面讲讲《马伯乐》。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鲁迅,当他问及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的时候,鲁迅列举了……等等人,最后说到:“田军(就是萧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当然鲁迅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后来的《马伯乐》或者是《呼兰河传》,但是我在这里说一句自作聪明的结论:我觉得萧红的写作呼应刚才鲁迅这句话,萧红用《生死场》表明了她是萧军的妻子;她用《呼兰河传》表达了萧红自己;她用《马伯乐》印证了在鲁迅去世之后所有人都送给萧红的一个头衔,就是“鲁迅的学生”——岔开一句,我最近翻萧红的全集,才发现萧红脍炙人口的《回忆鲁迅先生》那篇长文,其实她写了好几遍。大概是从鲁迅逝世三周年开始,接受媒体的邀请,一篇一篇短文这样叠加,好多事情是反复写的,都是很琐碎的,比如说鲁迅先生对紫衣服黄外套的厌恶,鲁迅先生踢鬼的故事,鲁迅先生抽烟,鲁迅先生吃饭,各种细节。
这就是萧红的天赋的能力,对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极其的重视。有的时候这一点也不见得是性别的差异,因为男作家里面也有这样重视细节的人(比如沈从文与汪曾祺),女作家也有很多大而化之,像丁玲的小说,其实就不太重视这些细节。所以这也不是一种性别的差异,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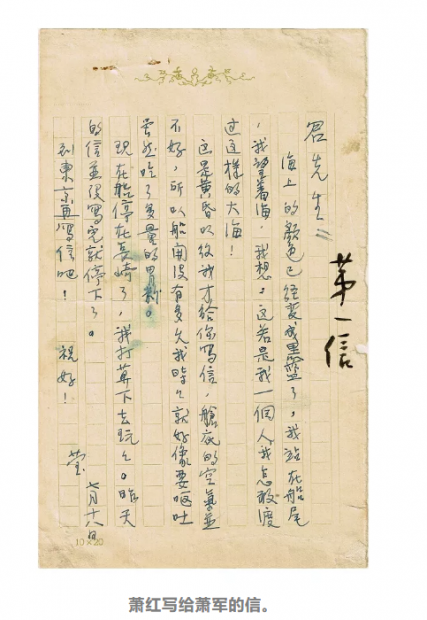
我说萧红用《马伯乐》证明了自己是鲁迅的学生,如果不解释的话,大家可能会很自然想到启蒙、国民性批判、讽刺等等这样一些词句上去(江河就曾经拿萧红跟张天翼他们相比)。而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说的。陈童在讨论时提到过逻辑化的问题,逻辑化的问题其实真不是一个性别的问题,而是一种我称之为战时思维,或者叫战争思维,就是当两个阵营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采取这种把一切都逻辑化、因果化的思维。
但是一旦你挣脱出这种二元对立,你很可能会感知到不一样的东西。之所以说萧红是鲁迅的学生,在于她的作品里面除了向鲁迅学习的那种对国民性或者庸众心态的某种冷静的讽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她继承了鲁迅的“不自信”。
鲁迅的作品里面其实有几篇技巧很圆熟,但是我并不太喜欢的,比如说《肥皂》《高老夫子》《离婚》,我都不是特别喜欢,因为在这些小说里面,鲁迅对人物有一种很强的间离感的,或者说就是为了讽刺而讽刺的。我可能更喜欢鲁迅《孤独者》《在酒楼上》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差异,可能就像鲁迅比较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和谴责小说的区别一样,就是“有没有共同忏悔之心”。当你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你是倍加自信,斩钉截铁,说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还是觉得犹犹疑疑,不能够真正说清楚这人物这事情,就像《祝福》里的“我”面对祥林嫂的质问一样,不那么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的本分。因为给出明确的答案,完全可以由政治家或者哲学家,甚至历史学家来完成,但是文学家不是这样的,作家的本分是要探知世界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好的作家都是要保持这种不自信,而不是采取一种冷嘲的、特别优越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来描述他笔下的人物和社会。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一直不太喜欢《围城》,也不是太喜欢张爱玲的很多作品,就在于作者在小说里都表现出一种上帝式的视角,好像已经把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概括在自己笔下了。相反,不管是鲁迅写《在酒楼上》《孤独者》,还是萧红写《马伯乐》,他们对这个人物的好与坏,其实是非常不清晰的。比如马伯乐这个人,可以说他是个巨婴,也可以说他是个渣男,他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但是,即使拥有了这么所有的缺点以后,萧红并没有抛弃马伯乐,她仍然将自己很多逃难时的孤独、幽闭、难过,各种各样的体会,放在马伯乐的身上。萧红仍然爱这个人物,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马伯乐就像萧红一个不争气的弟弟。曾经有评论家指出,为什么萧红要用一个男性的视角来写这个故事?其实这也是很有意味的一种选择。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不确定。

如果您还不明白的话,再举个例子,比如汪曾祺的小说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法,“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这地方有这么一个习俗?”而往往作者的答案都是“不知道”。你提出来问题,又不知道答案,你问它干嘛?这就是我说的作家在探索世界的可能性,他在探索的时候,他是不自信的,他提出来,他并不负责解答,并不负责解释。
他们面对写作对象的时候,不管你是嘲笑也好,讽刺也好,还是悲悯也好,其实都在表达这样一种不自信的态度:我不是很清楚,我跟我笔下的对象是平等的,他身上的弱点我们都有,处在同样的状态,我们未必能够做出比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我读《马伯乐》,印象很深的,就是在淞江桥的时候马伯乐突然一下就空了,不管小孩、太太还是细软行李,他突然就被无数的思绪给击倒了。马伯乐是一个弱者,或者说他是一个善于逃避的人,但是他的这种逃避和懦弱,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情绪,这是当一个普通的人不可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时,产生的一种自然的无由的恐惧感。
张爱玲在小说里面不怎么描写这种恐惧感,但是她会写在散文里面,经常会使用像“来日大难,舌燥唇干”或者是“惘惘的威胁”这样的描述,只不过她用一种很聪明的方式表达出来,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样,其实未必不是自己的恐惧。整个民国后期,这种恐惧感笼罩着时代。而萧红在马伯乐身上,是非常坦白地承认了,而且是放大了这种承认。这恰恰跟当时狂喊着“抗战建国”这样一些口号式的奋发描写,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让人想起鲁迅在《故事新编》的《非攻》里面写的墨子到了宋国,看着他的一个弟子在高呼说“我们都去死”“让楚国看看宋国的民气”,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像墨子他们,会这样做。小说最后的结果,是拯救了宋国的墨子,在宋国被搜检,仅有的破包袱也给募捐救国队募走了,他还碰上大雨,被巡兵赶出城门洞,“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我觉得这就是鲁迅的传统,鲁迅能够从大里面看见小,从神圣里面看见卑贱与悲凉——当然你也可以说张爱玲的金句,什么“华美的袍子下爬满了蚤子”,也是这种,但是这种总结性的东西,其实是很轻的。真正的人生的悲哀,一个人在时代当中无所措手的这种悲哀,都体现在那种琐碎的小事里,是马伯乐踢开房门倒下的瓶子,是他每天去买的未必居的包子,江轮上大家望汉口钟楼像望自由女神那样的逃难心态,是从这样的细节里面传达出来的。

所以我自己还是很喜欢《马伯乐》这部作品。但是,也许有人更喜欢另外一些。我们不强求,但是,我觉得大家能够去体会当时萧红的写法,而不是仅仅根据一些评价或者传闻,就把它随便地扒拉到那种“萧红不成功的作品”堆儿里。
好吧,今天够长了,就说这些,我们下周还有一期萧红,就要转入张爱玲了,我们下期再见。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