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今天点评两位年轻人的读城,一位1998,一位1994。
钱钟书说过,人年轻时没什么想象力,一到老年,想象力却变得丰富到可怕。
准确地说,年轻人有茫无际涯的想象力,比如敲锣,比如应援。
但是大部分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将想象力照进现实。所谓好莱坞将假事拍得像真事,中国电影把真事拍得像假事,其实就是想象力与现实的平衡关系。
故事可以假,细节必须真。名字可以假,人物必须真。年代可以假,逻辑必须真。
年轻时没学会哪些必须真。老了就全假。只剩下情绪是真的。
朴微这篇,有前辈说写得棒,我也认为写得不错。“像外国人写的”这个评语是双向的,作者自己说“旁观感陌生感”,这是外来眼光的长处,亦是短板。其实,以今视古,也是会带来这种外来视角的。昨天听编辑说,现在任何海外汉学的书,中文版都需要竞价了。这说明市场很认可这样的研究方式,一方面给人新的视角新的方法(但基本不会有新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黄永以前总说的西方学者“擅长讲故事”,让读者获得不费脑子看学术著作的满足感。具体到朴微这篇文字,借助城市布局切入,到家国同构,到阶级分野,再到“中国人的智慧”,确实有着联想的丰富与结论的剀切。可是太明晰的结论总让人疑虑,之前评陈童时也说到过这一点。详细地说,南宋行在对城市管理的放松,是有意还是无奈,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前提是这个王朝存在了150年,那它必须会在权力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君权、相权与绅权,还有农工商的权力,会形成一种新的模式。近几年中唐之后的政治成为研究热点,也是基于这一点——不然它们早就亡了。而这种新的平衡是什么,过往的历史叙述是忽略的,高宗之后,南宋诸帝的面目都相当模糊。如果说超脱我们通常理解的政治权力博弈之外的因素,南宋最值得注重的变化,一是理学的兴盛,二是商业的发达。前者带来道统与政统的抗衡,后者则支持并催化南方王朝的繁盛直至奢靡。一个靠商业而非农业支撑的王朝,一个商业城市的首都,各种逻辑都有着巨大的不同。比如,临安一门一户很多,传统的家法与族权在这里有多大的作用?人口的流动,保甲连坐能否贯彻?我昨天说过,饮食、垃圾与治安是城市最严重的问题,我们讨论一座城市,最首要的恐怕是要弄清它是怎么解决这三桩问题的。而对整个社会的三分法,看上去明锐得像一把刀子剖开黄油。但具体去套临安,我也不能无疑。这一点从我们自身的经验可以探知,凡经济发达的区域,不可能清清楚楚是中上层一套风气,下层又是另一套风气。首都民众的问题向来是见多识广,知道什么是耗财买脸,但经济实力大多数人无法从心所欲。清代人说京师民众“喜说大话,使小钱”,就是这种风气的表现。但临安是经济发达的都市,挣钱机会大大增强,流动性亦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都市对控制的挑战,这种情形下会滋生出多少新的挣钱方式,从改革开放一路走过来,太能想象了。而结合中国人的特性,弱者很擅长向更弱者抽刀。首都人的优越感,从嘲笑外地士夫不会吃饭就能看出来(让人想起《怯洗澡》)。那天看赵园老师的一句话”我们因为自己的限制而成为自己“,深有感触。在明了那么多不确定性之后,对临安这个13世纪的庞然巨物,空前富足,空前自信,也空前脆弱的首都,能够下的判语还真不是那么的多。在引用《武林旧事》或谢和耐时,需要时时想到作者的身份,作者的时空,以及作者的限制,当然还有我们自身学力、经历、思维的限制,所有的限制加在一块儿,才能形成”自己的临安“。“左邻右舍都说,王秀才算得上是个乐天知命之人。”我很喜欢这个开头。不知道作者这种“讲故事”的选择,跟我在领读时的建议有无关系;我也不知道王惟庸的故事是否纯属虚构。不过,以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串起日常生活的叙事,再从日常生活的热闹缝隙中窥见大历史的必然与偶然,正是一个卑微的写作者面对浩渺的历史长河,所能寻得的最佳方式,我以为。历史的想象力是最宝贵的,请小心收藏。说白了要重述故事,需要一个抓手。道理大家都是懂的。这种写法,重点是细节的穿插与运用,要用想象力来弥补其中的空白。这是我说的历史想象力。(白水:一两月前,看过一篇阿忆先生讲如何拍城市宣传片的文章,讲到一种方法,大意是选取一个有些特点的人的视角,如写城市便民,找一个残疾人;写国际化大都市,找一个外地人或外国人。记住这个人,可能更容易亲近这个城市。)难点在于怎么写出这个人物的“能动”而不仅仅是“接受”与“观看”。(魔菇:说到拍摄,今天正好论证了一个拍摄项目,个人观察,发现优秀的创作后面最核心的是对事物(文本)的了解和理解,还能在有限的创作空间中寻求最佳,这个需要创作者有很强的自尊心和意志力,可是当下糊弄了事就能过得不错,至臻的动力就少了。)正在校稿的《共和是》里,我也写了一些小人物:一个京师大学堂毕业,却参加宗社党意图反民复清的金先生;一个千里往返上海武汉四川,只为了寻回旧主端方头颅的马弁;一个恩平的年轻人,他成为史上第一个港督刺杀者,起因是港英政府禁止使用中国钱……昨天梅子酒录音里提到“巅峰体验”,其实我写史最美妙的体验是“历史就在我身边”的感觉。觉得要写这些“小大之间”,才不辜负这本书的副题“1912传”。我26岁时还在吭哧吭哧写晦涩难懂的论文,如《帝国天空最亮的星——本雅明与机械时代》之类。两年后开始写《野史记》,这本小书的修订版2019年还能销出5000册,不知道是不是好事。
话题: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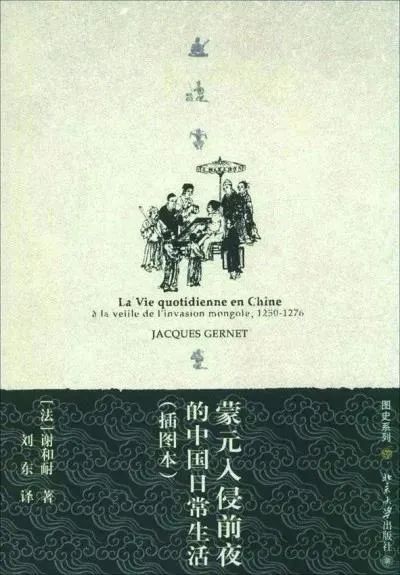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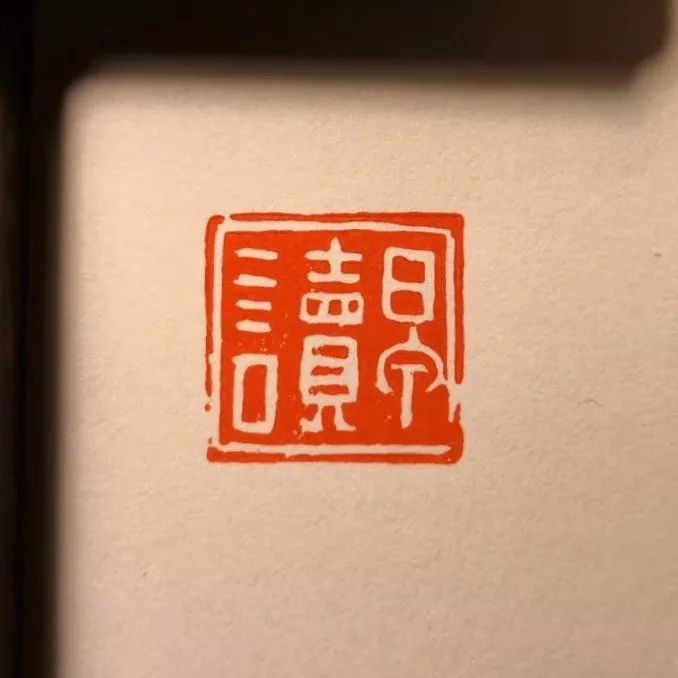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