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现代中国》有位共读者,最近发了一段感言:
2019年阅读邻居共读“小说民国”的成果,《小说现代中国》,在两年后的本月诞生了。编校过程我有参与过一次,除了校对老师和其他共读者的发言外,做的最多的就是大刀阔斧删改自己的发言,甚至直接在旁边给编辑老师备注‘是否考虑整段删掉?’自己写的东西无法说服自己让人非常痛苦。
这几天重读本书,读到自己的部分后我又忍不住边读边在心里改,而后又突然放手,对有意或无意造成的言不及义的纠结与痛苦,也算是为数不多至死方休之一种吧。
我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能够完全理解别人的痛苦,只能猜测与共鸣。“自己写的东西无法说服自己”这种痛苦我也有过,很多回。用我的话说,就是感受不到诚实面对自己的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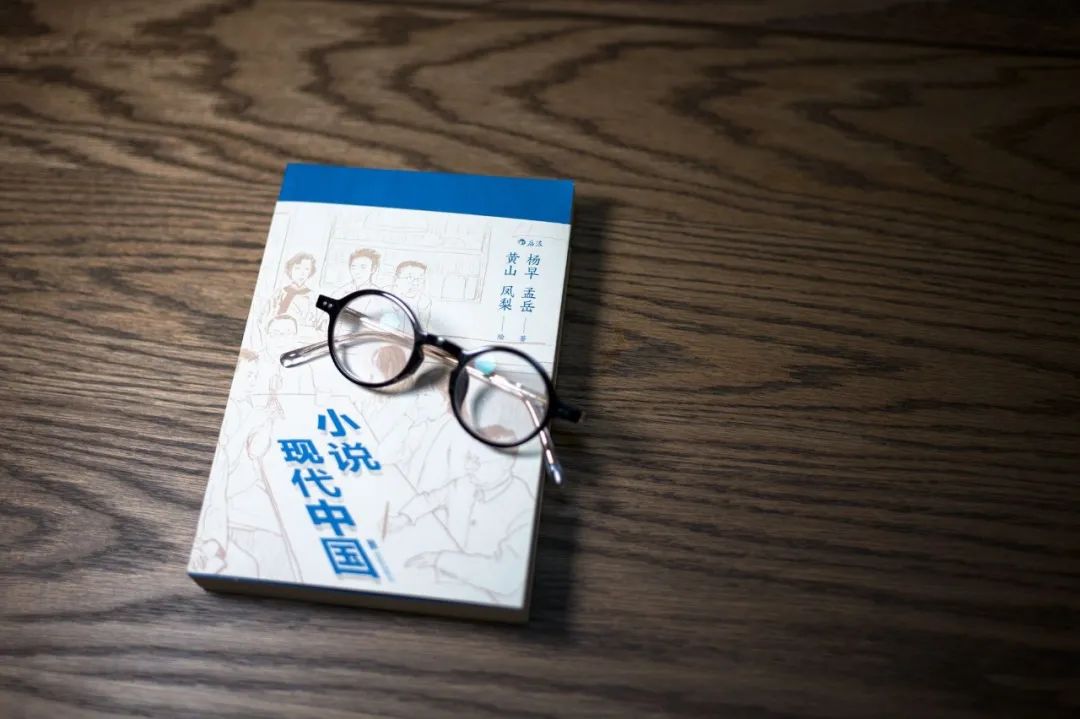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说每一次写作,作者都必须面对特定的拟想读者。如果这次写作是非功利的,只是有话要说,那它的拟想读者就是作者自己。但是大多数场合,写作的第一拟想读者都不是自己,而是领导、同行、编辑、消费者及各种委员会。在这些场合中,写作的第一使命就不再是宣洩或表达,而是揣摩及讨好。模仿康德的话说,写作不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之所以不想把这事称之为痛苦,因为这种感受与敏感度与追求有关,不一定是痛苦,也可以是冷漠麻木无感,甚至也会有迈向成功的愉悦。在我看来,这种写作主要的问题,是感受不到诚实面对自己的快乐。
小的时候我跟大部分同类一样,感受不到诚实会带来快乐。毕竟如果你向周围的家庭学校诚实说出所思所想,一般只会收获轻蔑与怒斥。亚里士多德说控制不了自己欲望的人就是奴隶,一般人为奴十八年,就已经习惯了不再对世界诚实。人年轻时候为什么特别需要朋友,可能是因为朋友没有立场与资格批判自己,相处时还能残留些许诚实。
对外界不诚实的时间长了,对自己诚实也就变得艰难,谁也不想陷入一种分裂的思想状态。于丹老师总说不能改变外界,就改变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能够表里如一地不诚实,那他就是诚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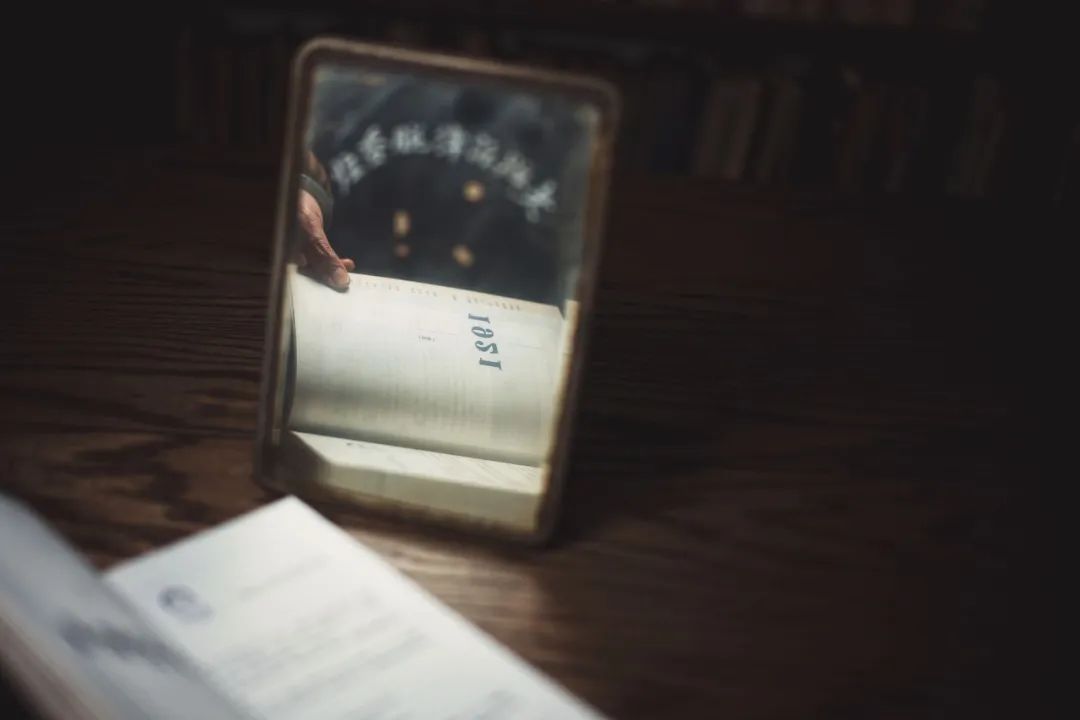
那如果诚实面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快乐?我也说不出来,像我现在写的,肯定不是为了自己之外的目标而写,我就想诚实地说说不诚实的难受。像上面那位共读者,民国小说共读当然没有任何的考察或通过标准,按说是可以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但是一个人习惯了不诚实面对自己,TA写每一个字说每一句话,可能都会先考虑别人看到会怎么想,这段话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人设改变。这种习惯并不庸俗,甚至高尚:有时我们是希望别人眼中的自己更好更完美,有时只是为了希望爱我们的人不要伤心或担心。
它唯一的问题是:感受不到诚实面对自己的快乐。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