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能不能上桌吃饭”的争论一出来,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都快疯了,完全理解不能——既无法理解这种“陋习”为什么还能存在,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不少人为之辩护。
其实,换一种立场,很容易理解辩护者的思路。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可以用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来概括。差序格局的特点,包括确立家庭中心,维持秩序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实行“长老统治”等等。我们观察“女人不能上桌”的实例,确实可以从中看到差序格局的运作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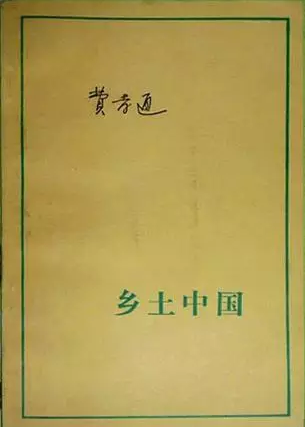
费孝通《乡土中国》提出的“差序格局”概括力很强,可以帮助我们认知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全盘奉行儒家文化,但在“名分”和“规矩”这两点,儒家文化与传统社会最合拍,也最招人迷恋——《弟子规》这种单向要求的下一代守则会被捧为“国学经典”足以说明这一点。“安分守己”是儒家伦理生活化的中心点,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要引鲁迅那段熟得发烂的话: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灯下漫笔》)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有些人说并非日常,而是在客人上门时。恰恰是这一点,反映出“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实质:在家庭交往构成的社会交际中,其实也讲“对等外交”,对方派出的是家主,己方自然是家主陪同,而在传统社会里,家主被默认为主事的成年男性。如果是王家大婶李家二姐来串个门留个饭,断没有家主出面陪同,妇幼另桌吃饭的道理。
不管你喜不喜欢,传统社会就是这样,而且运转有效,而而且,不仅中国如是,西方也照样。即使他们已经开始搞民主政治,妇女还是长时期没有选举权,何故?身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男性家主代表全家意见足矣。这就是“规矩”或“传统美德”的来源。
不过,话要两头说。东晋谢安欲纳妾,夫人刘氏不同意。谢安的侄儿们都跑去刘夫人面前背“关关睢鸠,君子好逑”,因为《毛诗》说此诗喻后妃“不忌之德”,刘夫人问:这诗谁写的啊?大家说“周公”,刘夫人道:周公是男子,难怪写这个,“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
这个故事很说明“长老统治”权力结构的复杂,不仅包含“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包含“民主的同意权力”,还有“教化权力”。刘夫人不同意谢安行使夫权,男性亲戚就跑来行使教化权力,刘夫人很厉害,提出了“谁是本位”的问题。
在“女人能否上桌”的争论中,并非外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质疑,而是内生性矛盾,在内心里一齐掀桌的女性,行使着“民主的不同意”,那些强调“规矩”或“传统”的论者,是在行使教化权力,但这些规矩或传统,在掀桌女们看来,都是男性本位的规则。从女性本位出发,她们要争取家庭内部的尊重,同时也在争取向外的表达权。
梁实秋曾撰有《请客》,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他为男女主人各自安排了职司:男主外,也是发起请客的主体,考虑的是请谁,“把素未谋面的人拘在一起,要他们有说有笑,同时食物都能顺利的从咽门下去,也未免强人所难。主人从中调处,殷勤了这一位,怠慢了那一位,想找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亦非易事”。毕竟是现代社会了,梁实秋也强调了“妇主中馈,所以要请客必须先归而谋诸妇”。可是,工作是男人的,社交是男人的,面子是男人的,情感投资的回报,当然是男人的,但也是整个家庭的,所以主妇但凡力所能及,能反对的理由实在不多。
动手操办呢,势必落到主妇身上,“家里有厨师厨娘,自然一声吩咐,不再劳心,否则主妇势必亲自下厨操动刀俎。主人多半是擅长理论,真让他切葱剥蒜都未必能够胜任”。司中馈的主妇,哪里有上桌的时间与精力?只有在将近尾声,已经有人先走一步了的时段,女性才有露面的机会,“这时主妇踱了进来,红头涨脸,额角上还有几颗没揩干净的汗珠,客人举起空杯向她表示慰劳之意,她坐下胡乱吃一些残羹剩灸”。请客请完了吗?当然没有!“地上有无数的瓜子皮,纸烟灰,桌上杯盘狼籍,厨房里有堆成山的盘杯锅勺,等着你办理善后!”谁来办理善后,默认设置又是主妇!
看到没有?“女人不上桌”并非只是农业社会的习俗,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它依然长期、广泛地存在。能承担做菜不上桌的女性,会在社交圈中有贤惠之名。即使今时今日,它仍是很多家庭的常态,我们的父一辈当年请客,不都是这样?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之后,越来越少在家里请客,此时蓦然在“城乡差异”的背景被提出来,而且加以“强制”“掀桌”的修饰放大,显得触目惊心罢了。



“女人能否上桌”其实是个双方合意问题。核心家庭达成协议或默契,谁主外,谁主内,只要双方无异议,旁人不必置喙。延展到大家族,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所须反对者,是天然地将弱势的、隐身的、出力的角色,派发给女性,并用“规矩”或“传统”来压服不同意的女性——在女性已经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今日,这无疑是一种显豁的歧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是没错的。这社会也不都是追求独立实现自我的女性,想跟对人嫁对郎少奋斗几十年的大有人在。嫁入豪门的女子,要守得规矩可能比农村还多还苛,却无人说话,背景换成城里媳妇农村郎,这些矛盾马上都凸显出来,这也是社会分裂的征兆之一。
这一点,看看网络文学里的女穿小说就知道。比如种田文里,穿越到农村的女主要奋斗要改变自己命运,除了向爹娘宣传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外,挖空心田酿葡萄酒找玉米种发明新菜,取得经济独立,才是独立自主反抗宗法家族制度的前提。而那些穿到深宫大院的贵妃太子妃们,完全不操心生计收入,想的就全是打倒对手争宠宫斗了。这或许就是费孝通的“特殊主义伦理”吧:“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

本文首发于 腾讯大家 Ipress,谢绝一切非授权转载。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