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正式去三联上班。
到底去哪一个部门,还没有定呢。
……我也笑笑,情知差不多就是这样了:去《读书》。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往社科院,先找郭一涛,然后同往院人事处,取得商调函。
午后往永外办调离手续,取得档案。
将档案送到院、所。
黄昏微雨。
《〈读书〉十年》是名物学者扬之水(又名赵丽雅、赵永晖)1986年至1996年这十年的日记选编。这十年,正好也是扬之水任职《读书》编辑的十年。旧版于2011年由中华书局开始陆续出版。倏忽又是八年过去,新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增加《友朋书札》一册。重读是编,仍然是八年前的滋味:百感交集,迭有所见。
当我又一次重读《〈读书〉十年》时,想的不再是“我从这套书里看到了什么”,而是“这套书会带给不同世代什么感受”。
时至今日,1986年出生的孩子,现在是社会中流砥柱,1996年出生的,也已经大学毕业。不过我相信,任何世代的读者,只要对近三四十年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有所体认与记忆,就能从《〈读书〉十年》中读出不同的况味。将来的后生,能够从书中获得的益处,只会更多,因为《〈读书〉十年》正如我当年为旧版撰写的书评,是“十年日记,百科全书”。
1 学者的个人成长史
扬之水近些年在读书界可算声名赫赫,其著作举其大者,即有《诗经名物新证》《诗经别裁》《先秦诗文史》《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奢华之色》(三卷本)《棔柿楼集》(十卷本)《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三卷本)《物色:金瓶梅读“物”记》等等,是实实在在的著作等身。
而这样一位饱学硕儒,是如何养成的?且不去说“初中毕业”“卡车司机”这类江湖传闻,以免制造又一个逆袭神话。单说她能在1986年进入《读书》编辑部当编辑,可以见得当时人才稀缺之一斑,文化界又正好还在百废方兴的当儿——时代在剥夺了扬之水这一代人青春向上的机缘后,又给出了一条亡羊补牢的幽径。自然,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不是之前在《读书》发表过文字,初中生赵永晖也无法进入沈昌文领导下的《读书》编辑部,成为后来名传一时的“《读书》五朵金花”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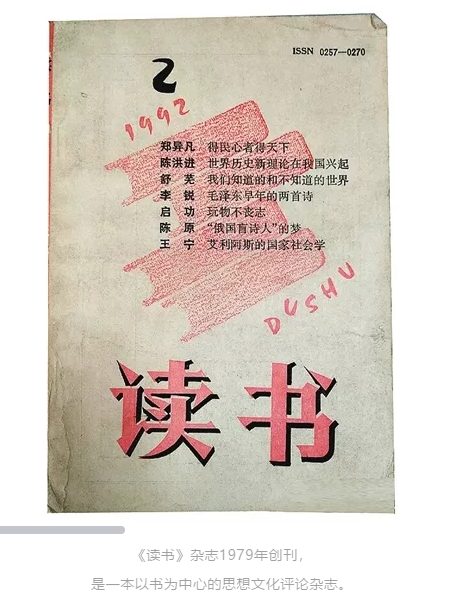
《读书》当时的主编沈昌文在《序》里说:“她年轻,肯走路,于是经常派她出去取稿,实际上做‘交通’。这方面她效率挺高。但更令人意外的是,她所交往的作家学者,对她反映奇佳,因而效果也十分特出……我到了多年以后才知道,她是把同作者的联络当作一种‘师从众师’,所以十分得益。”用扬之水自己的话说:“对编辑部诸同仁来说,编《读书》,不是糊口的职业,而是一份爱好,一份生命的寄托。”不妨说,是《读书》十年中的无数作者,共同培养了扬之水这样一位学者。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可以算是“初访辛丰年”。辛丰年先生当时居南通,较之京沪两地作者,见面自属不易。扬之水于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借去沪之便,专程赴南通访辛丰年。早晨六点半敲响房门,两人进入“一见如故”模式,“彼此谈过身世经历之后,就谈历史,谈音乐,谈书法,各类话题穿插跳跃,无所不谈,几无间断”。到扬之水下午四点二十分登船返沪,“整整谈了十个小时(其间很少停顿),真是口舌干燥,嗓子都有些沙哑了”。这等奇观,初见双方如果没有此前联络交流产生足够的信任与认同,哪里有可能达到?

《读书》需要接触的作者极多,几尽学界一时之选,扬之水自然也非人人“平等交往”,但她像海绵一样,总是能从“众师”那里获益。例如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读书沙龙第一次活动”,讨论的题目是“现代性危机:各种可能的解”,参加者达十二人之多,包括汪丁丁、何怀宏、徐友渔、刘军宁等。扬之水自言“对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但作为一个观察者,看大家如何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了解每个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及在争论中的姿态,倒是挺有意思的”。
正是通过这十年《读书》编辑的转益多师,扬之水终于下定了投师孙机、从事名物之学的决心。《〈读书〉十年》日记今分为四册,一一展读,可见作者的学术兴趣,从漫无所依到“定于一”,有一个很明显的过程,如以今之学院训练比附,则相当于硕士至博士前期的确定学术方向,终于,在一九九五年九月六日,扬之水记下一段:
读孙著,并与先生一席谈之后,痛感“四十九年非”,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只是前面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是不多了,更生时光促迫之感。
从日记看来,正是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与内心的紧迫感,成为促使扬之水离开《读书》转往社科院的主因。从此中国学术界增一好学者,而文化界失一好编辑,得失难言,局外人只能为扬之水本人贺。
2 八九十年代的生活史
周作人于一九二五年三月曾作《日记与尺牍》,开篇便道
“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地表出作者的个性。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人,日记则给自己看的(写了日记预备将来石印出书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
周作人这番话,移来评《〈读书〉十年》,再确当不过。《〈读书〉十年》旧版为三册,新版将日记析为四册,并添一册《友朋书札》,凑成完璧,无论是对于扬之水的个人史,于《读书》的成长史,更重要的是,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史与物质生活史,也是一批绝妙的脚注。
正如周作人所言,每个人的日记与尺牍,都鲜明地表出个性。扬之水日记的个性,首先在于记录所注目与过滤者,与旁人不同。近代人物日记多有出版者,但像《〈读书〉十年》这样,于交游、物价、食肆、菜色,无所不记者,尚属绝无仅有。《读书》主编沈昌文爱吃,亦有“首先抓住作者的胃”之隽语,故《读书》编辑部虽小,与作者、同行各种聚会,几乎两三日必有一至数起。偏生撞到扬之水不仅重古之名物,今之食事亦一并详记,《〈读书〉十年》,随手揭开,无处不见食于何处,与何人食,是何菜品,饭价几何。于是读者才知道九十年代的必胜客,五人可以吃到八百多元;赵萝蕤热爱肯德基,数年生日均由扬之水买炸鸡往家里庆生;而彼时各地之面价,或五六毛,或两三元,都能反映当日各地之经济发展状态(有云每平方米适宜房价,当为一千碗牛肉面总数)……如此细数琐计,不胜枚举,倘有心人,将这些记录一一整理,对应相关社会史料,大可为八九十年代物质文化史,开一生面。

至于友朋笔札,当然首先基于《读书》的编著往来,但扬之水既是如此妙人,来函诸公自然也放开心怀,学术、出版之外,谈天气,谈饮食,谈音乐……当真是“见字如晤”,各具面目。其中雅趣,可以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一则日记为例:
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于是将此数语抄与何兆武、周黎庵、周一良、朱维铮诸先生,就便约稿。
风雅之极,堪谓当代《世说》之属。难怪黄裳看过部分日记内容后曾致信作者称:“因叹尊藏日记皆逸人韵事,可辑为一册,可惊俗目,又知足下为编辑时,辛勤周至,无怪为作者所胜赞,如此编者今无之矣。”日记与尺牍,于此恰可互补,可惜未见扬之水致诸公手札,否则往来鸿雁,更能明晓何谓“如此编者今无之矣”。
《读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影响,不必在此讨论。《〈读书〉十年》中记了叶秀山的一番谈话,说“《读书》是‘后学术’,能写书,能写论文,能把自己的专业玩熟了,才能给《读书》写稿”(一九九四年一月廿五日)。说《读书》是沟通连接这一时期知识界中心与边缘,主流与另类,先锋与保守之间的媒介,并不为过。有意思的是,《〈读书〉十年》基本不记“会议内容”,反而将大量笔墨集中于学人交游,轶事趣闻,饮食日常,与《读书》杂志本体的关系,或近于一种“祛魅”的关系,廿余年后读之,倒真有一种难得的清醒。
而同时代的文化热点与事件,在《〈读书〉十年》里留痕不少。如气功热,文化热,旅游开发热……扬之水不喜欢张艺谋,但每部张艺谋电影也会随俗往看,喜欢姜文、张爱玲、须兰,颇多赞语,也呼应着时代的幻彩。尤有意思者,扬之水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像是第一次坐飞机”,觉得好玩极了,接下来是一大段颇有童心的描述:
忽悠一下便腾空而起,简直像神话一样,快乐得差一点笑出声来。受气流影响而引起的颠簸,也给人异常舒服的感觉,要是能翻个跟头就更好了。坐在里面,几乎感觉不到行进,可一个小时之后,就听到广播说马上要到首都机场,遗憾太短了。

莞尔之余,想到前一段网上热传的“中国还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转觉社会生活之变动,在偌大中国似乎总是落差远超想象,而事实上,我们的时代,必须有无数碎片构成的拼图,为之画一幅肖像。无论何时代人,都应该感谢扬之水,用她的工笔,为这十年留下的一部个人史兼“日知录”。

原文首发于《光明日报》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