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今天要讲的这本书,是任继愈先生所著,叫做《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和事》,是从任先生不同的文章,或者访谈中截出来的。
所有的这种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儿,大部分我们都知道。但是,旧瓶也可以装新酒,一些可能耳熟能详的轶事,在今天来看,心情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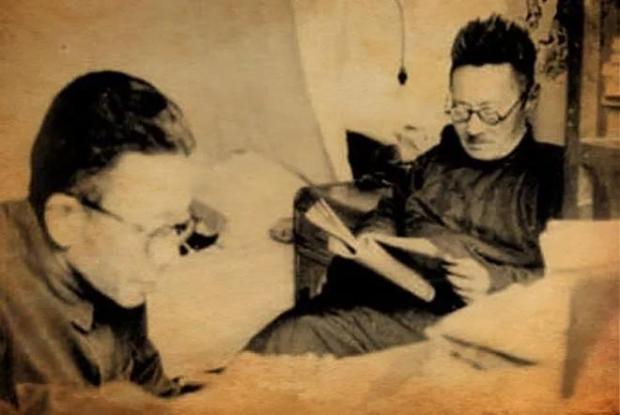
刘文典
首先想讲的是大家都很熟的刘文典先生。书中说:“刘先生平时对学生、对同事礼貌待人、彬彬有礼,他看到他不喜欢的人,真是当面让人下不来台。”举的例子,当然就是刘文典在躲警报的时候见到了沈从文,当然书里只说“平时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
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
任继愈评价说:“魏晋时,阮籍用青白眼对待不同的客人,刘先生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
问题是,西南联大到底应不应该聘请沈从文当教授?沈从文又是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我也没有答案。包括沈从文教出来的学生汪曾祺,也是因为不爱系主任做的学问,不能讨系主任的欢心,所以最后没法留校。
但是之所以西南联大会成为一个神话,比抗战别的高校,比如说华西坝五大学、西北联大、浙江大学这些高校要更有名,很大程度上跟新文学作品,包括沈从文、汪曾祺、宗璞,有很大关系。
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刘文典先生这种“我不喜欢的,就不应该存在”这种心态,其实是既不自由也不包容的,跟任继愈的书题《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的人与事》完全相反。
书中还提到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刘文典其实非常崇拜陈寅恪。他曾经说过“作为教授,陈寅恪应该拿400块钱薪水,我应该拿40块钱,沈从文只应该拿4块钱”。但是他有一次跟陈寅恪争得很厉害,他们争的是什么呢?他们争的是“谁的身体更差”,相持不下。最后刘先生说:你只穿了一件皮袍子,我穿了两件皮袍子,可见我的身体更差,“自得之色溢于眉间”,陈寅恪不再争,服输了。
请问拿穿两件皮袍子来证明自己身体更弱,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实在不懂。除了说明刘文典这个人争强好胜、性格古怪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韵事可言。
还有一则说刘文典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因为周作人说,作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啊,不管制作包子的厨师是否强奸过他嫂子”。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强奸过他嫂子的人能做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我实在想隔着时光反问一声刘先生:怎么就做不出来呢?一个作家的人格,和他的艺术才能不成正比,这是常识。如果你迷信“文如其人”的话,你就上当了。
所以,我觉得刘文典先生,是一个“不包容”的典型,他跑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说明他负载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有好有坏,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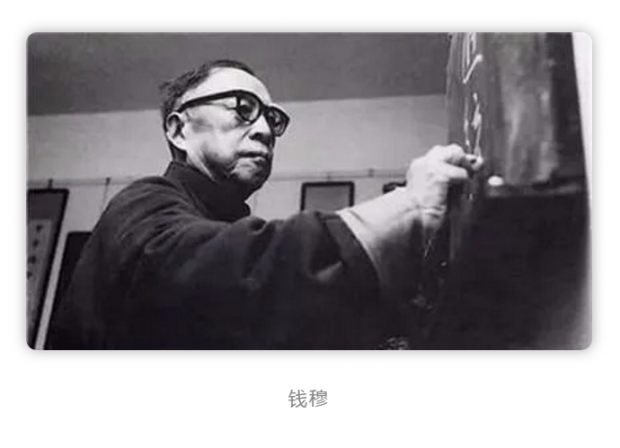
接下来说说钱穆先生。钱穆在抗战的时候出版了《国史大纲》,扉页上题词“献给前线百万将士”,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钱穆先生爱国当然没问题,但是由于爱国,所以他在《国史大纲》里就不断强调“中国文化怎么怎么好”。任继愈先生在书里也谈到过,因为他夫人冯钟芸是冯友兰先生的侄女,参加过历史教材的编写,任先生引用章学诚的话说,“欲亡其国者先亡其史”,所以他说教科书应该增强学生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但这句话不能反过来,不能说教材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为了提高学生爱国心和凝聚力,那样的话就没法看了,因为必然而会造成某种遮蔽。中国的漫长历史里面,可以说什么都有,我认为“了解相对全面与真实的历史”更为重要。
我最近在读一本穿越文,主角穿越到崇祯元年,以一篇《少年大明说》参加科举,夺得县试案首,“美哉我少年大明,与天不老;壮哉我大明少年,与国无疆”博得了陈洪绶与刘宗周这样的大儒青睐。如果你懂一点科举史与近代史,你就知道梁启超这种报章文恰恰是反科举的。说到“亡其史”,我倒是觉得这样的知识传播是在亡其史。
书里还有一则轶事,说钱穆讲课喜欢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历史系的教授姚从吾对他说:“讲中西文化的异同,最好听听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这里有西方文化的精神”。钱穆因为没有出过国留过学,多少也有点受歧视,这一点同于沈从文。不过就这件事而言,钱穆有没有出过国,倒不是问题,但是如果对西方社会与文化不够了解,奢谈中西文化异同,肯定是有问题的。
钱穆后来竞选院士,屡屡受挫,跟他没有西学背景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当然有学界的某种歧视在;但另一方面钱穆的这种学术风格,也是会留下让人诟病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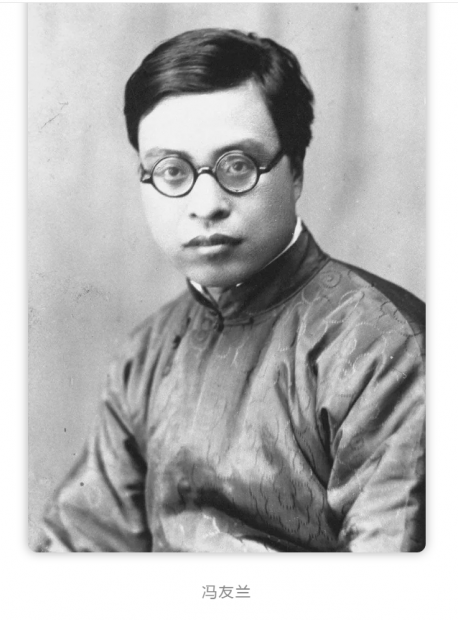
回过头又说到冯友兰,冯友兰也是出于爱国的责任感,所以他一直反对胡适说的“中国有思想史而无哲学史”。这倒无所谓,见仁见智。只是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里面讲他1982年去美国讲学的感受时说:、
他1946年到美国来讲中国哲学史,“像在博物院中当讲解员。讲来讲去,觉得自己也成了博物院中的陈列品了,觉得有自卑感,心里很不舒服。这次我来美国,虽然讲的也是中国的东西,但心情完全不同,自卑感变成自豪感,不舒服变成了舒服。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将来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
冯友兰的这些论断,是没有论证也难以论证,仅仅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最大的好处是让自己“自豪”“舒服”。这就好象在北大年龄这件事上,冯友兰也跟胡适唱反调。冯友兰一直主张北京校史不要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算起,而是从东汉太学算起,原因是:西方许多著名大学,动不动就几百上千年历史,我们中国最好的大学也应该有更长的历史。
说实话,我觉得冯先生的这些想法,虽然很可爱,但正如王国维所说“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冯先生自己主张,自己开心就好,但如果这样的思路定于一尊,不容置疑,那又哪里谈得上“自由与包容”呢?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